欲将沉醉换悲凉说晏小山
04-14Ctrl+D 收藏本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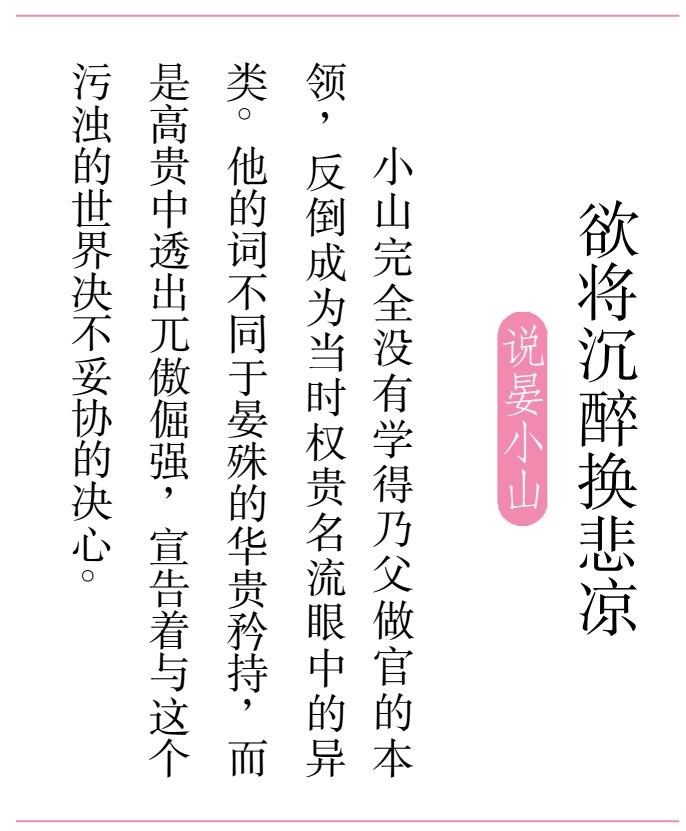

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会在心里为他熟知的文学家排一排座次,掂一掂谁是状元,谁是榜眼探花。有时候,这种排位只体现评论者的个人喜好,他在说“ 某某是最了不起的大诗人” 时,其实意思是“ 某某是我最喜爱的大诗人”。但如果评论者本身也是行家作手,他的排位就绝不可等闲视之,体现出的实是他的文学观。传统词论家都是词人,他们的意见当然值得重视。对历代词话做一粗略统计,对北宋词人的排位大致分作两派,一派推崇周邦彦,一派则推崇苏轼。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词集名《片玉集》,又称《清真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评价其集:
多用唐人诗语,栝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
这是从作词的技巧上推崇清真。
陈郁的《藏一话腴》则称:
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
这是自清真词的传播之广、受众之博而立论。
刘肃为陈元龙集注本《片玉集》作序,对清真同样推崇备至:
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欢筵歌席,率知崇爱。
旁搜远绍,“旁搜” 是指他擅长用典故,“远绍”则是说他擅于继承唐人的诗风。说他“ 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这简直是把清真比作江西派的诗人。这是针对他的语言风格典雅近诗,以及以学问为词的特点而言。
宋元之际,沈义父作《乐府指迷》,这是一部教人填词的著作,说:
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
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
同样是讲清真的风格典雅,语言醇正。
同时尹焕作《梦窗词序》,则直截了当地说:
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但对清真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竟然是早年非常不喜欢清真,称清真方诸秦少游,有娼妓与良家之别的王国维。王国维晚年作《清真先生遗事》,直把清真与杜甫并列: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王国维这样推崇清真,一个原因是王氏本身就不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词人,他的《人间词》理致苦多而情致苦少,故对于清真那些淡薄寡情的作品较能赏会;另一个原因则是他重视清真词的音律,却不知词体最初虽是音乐文体,它的文学性还得靠情感的浓挚才得建构。
另一派所推崇的是苏轼。王灼《碧鸡漫志》这样称说: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王灼的评价,着重在东坡格高调逸,所谓向上一路,指的是东坡对词的内容的拓展。从东坡开始,词就不仅是抒情的文学,更可以用来表现词人的思想。
南宋军事家、抗金名将向子諲 是一位豪放派词人,胡寅为他的《酒边词》作序,有云: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胡寅特赏东坡的“ 逸怀浩气”。逸怀是庄子思想的体现,意味着对尘世的坐忘与超越,而浩气则是孟子的精神,表现为对理想的执着坚守百折不回。胡寅认为词到了东坡,则花间词人直到柳永,都只配给苏轼当佣人轿夫而已。
推崇清真的把清真比作老杜。清代刘熙载则以为东坡意似老杜,格似太白,兼有二家之美: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而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王鹏运,对东坡的评价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 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王鹏运列数潘阆、宋祁、欧阳修、柳三变、晏几道、秦观、张先、黄庭坚、贺铸的词风,以为虽各尽其美,后人都可得而模仿,唯东坡堪称天才,无从模仿,无从追蹑。他认为词中苏辛并称,辛词虽亦影响巨大,但不过是人中的高境,东坡词却是仙境。他这样推崇东坡词,当然是把格高视作文学评判最高标准的缘故。
我在大学读书时,与同舍友陆杰就曾讨论过宋代谁的词最好的问题。我们观点完全一致,就是认为辛弃疾的词比苏轼的好。我们认为,悲剧是一切文学样式当中最高的文学样式,而辛词中激荡着无与伦比的悲剧情怀,是真正的崇高美,然苏词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悲剧情怀,因为他的人生观太豁达,悲剧意识就被这种放达的人生观所冲淡,到不了崇高之境。苏词格是很高的,但格高并不是好,真正的好,是能让人感动,是靠执着于人间的悲剧情怀让人感动。东坡什么事都能看得开,面对人生的悲剧现实,他不是选择傲然担荷,而是娴熟地自我排解,这样的人的性情,一定会浮于表面,他写不出最浓挚深婉的爱,也写不出最苍凉沉郁的恨。
而清真的词,我认为一点也不好。单看艺术技巧,清真的确十分高明,他首创了一种蒙太奇式的写作方法,用在长调里,只是通过镜头的转接,就完成了词的叙事,而淡化了时空的顺序,让读者随着词的意脉行进;文辞也典丽可诵,不像柳三变那样,市井气较重。但文学史应该是灵魂的历史,在清真词中,我们见不到感人的力量,因为它们太缺乏灵魂。
清真的根本毛病就在于,他绝大多数的词都是写众人的情感,比如说他写别情,写的是世人分别时那种普遍的情感,而不是写他个人独特的私密的情感,这违背了中国学问、中国文学的最高原则:为己。中国的学问是为己的学问,中国的文学是为己的文学,故修辞而立其诚,是学问、文章最基本的要求。做学问做文章,一定要说自己最想说的话;作诗填词,一定要写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要写个人独特的心理体验、生命体验。清真的绝大多数词,是写给他人的,写给大众的,是“ 为人” 的文学,是商业化的写作。
所以我赞同刘熙载的观点:“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论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何谓“ 当不得一个贞字”呢?这是说清真的心“ 不得其正” (见《大学》) 。须知道,文学创作一定要正心诚意,要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其内,才可能写出好作品。一切文学经典都必须是有病呻吟,若是无病呻吟,哪怕呻吟得再像,也是赝品。清真的词,就是高仿的文学赝品。
在千古词人中,我最推崇的当然是后主,而若于北宋词人中选出一位鳌头,我的票投给晏几道,这是因为晏几道真正是用生命在写词,他的词是由血泪凝成的红冰。
推崇晏几道《小山词》的人,放诸文学史中,绝对是少数。但我于古人中,也并非全无知音。陈振孙虽称清真是词人中之甲乙,对小山也不免左袒:
小山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其为人虽纵弛不羁,而不苟求进,尚气磊落,未可贬也。
小山词何以独可追逼《花间》,甚且高处或过之?这是因为,小山是一位有精神洁癖的狷者。他虽不似狂者柳三变一样放荡恣肆,却绝不肯苟且求进,终身捍卫着心灵的自由,故终身全心全意地写词,全心全意地爱,全心全意地恨,全心全意地歌,全心全意地哭,他的人格铸就了他的词格。黄庭坚说小山词“ 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精壮顿挫本来是诗的风格,以之来形容小山的词,评价已不可谓不高,更何况还能动摇人心?须知动摇人心就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只有其人与其作品合而为一,以生命为词,以情感的纯粹干净动人,这样的词才是值得一遍遍咀嚼的文学精品。
近代词人夏敬观云:
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山谷谓为“ 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chuì )” ,未足以尽之也。
夏氏结合小山的人生阅历谈他的词,指出小山词是以生命铸就,非常深刻,至于点明小山词有过人之情,更是知味之言。要知道,诗至缘情,无以复加,一位文艺家如果情感特别充沛,他人的文艺技巧再精熟,都没法与之匹敌。这样的文艺作品,只能用“元气淋漓” 四字来评论。所以我的观点是,单就词而论,东坡词不仅比不上小山,比起秦观来也颇有不如。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 淮海就是秦观 , 秦观自称为千古第一伤心人 ) 。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固已先我得之矣。
现代著名女词人沈祖棻 ,她的《涉江词》总体艺术成就极高,易安以后,一人而已,于文学也有独特的赏会,宣称自己情愿给晏叔原做小丫头,对小山的崇爱之情,可见一斑。
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父亲晏殊,既是官运亨通的太平宰相,又是一位著名词人。但小山完全没有学得乃父做官的本领,反倒成为当时权贵名流眼中的异类。他的词不同于晏殊的华贵矜持,而是高贵中透出兀傲倔强,宣告着与这个污浊的世界决不妥协的决心。
晏殊,字同叔,谥号元献,抚州临川人,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卒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七岁被乡里视为神童,十四岁以神童荐入朝廷,宋真宗亲自面试,赐同进士出身,三十岁就出任翰林学士,到了宋仁宗朝,就做到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即宰相。晏殊的气质很特异,被认为是“天生富贵”。据《宋稗类钞》记载,晏殊虽出身普通农家,但他的文章诗词,有天然富贵之气。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叫李庆孙的人写的《富贵曲》,中有“ 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两句,晏殊就嘲笑道:“这是乞丐相,根本没见过真正的富贵。我要是写诗咏到富贵,我不去讲金玉锦绣,我只讲气象。比如说‘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这样的句子才是真的富贵,那些穷人家有这样的景致吗?”
这种天生富贵的气象,实际上反映的是晏殊天生适合做官的性情。正因为晏殊的性情是恬淡的而不是深挚的,是冷淡的而不是激烈的,所以他才能做那么大的官,而且一生太平无事。在他身后,学生欧阳修为他制挽词三首,其中第三首开头就说:“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性格决定命运,能明哲保身,更多的是因为性情,而不是因为他正巧碰上好时代。三首挽词中第一首是五律,谈到晏殊的性格是“ 接物襟怀旷”,一个“旷”字,便是晏殊的性格密码,有这样性格的人,一生不会有过人的快乐,也不会有过人的痛苦。唯拥有这种性情的人,才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官僚,但拥有这种性情的人,却决计做不了第一流的文学家。
现代著名学者顾随先生说,中国诗词最动人之处,便在于“ 无可奈何” 四字。晏殊的名句“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无可奈何之情,本来最易动人,但由他写来,却丝毫不能给人以哀婉深挚的感觉。至于下面这首《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完全没有了《花间集》里对爱情的天真决绝,“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 (牛峤 《菩萨蛮》) 、“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韦庄《思帝乡》) 的至情至性,到了晏殊这儿,竟然成了“ 不如怜取眼前人” 的世故成熟,这正是晏殊作为官僚成功的地方,也正是他作为词人失败的地方。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晏殊便是太早熟、太不天真、太不像孩子,所以我们读出的是那个淡而寡味的富贵中人,而不是让千秋儿女洒泪西风的词人。
小山与他的父亲完全是两类人。
小山生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卒于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活了七十三岁,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晏殊过世时,小山才十八岁,他的内心太过兀傲不群,是以很快家道中落,一生仕途偃蹇,只做过推官、镇监一类的小官,完全没有他父亲阅历名场的一套本事。在他沉沦下僚的生涯里,还曾因为友人郑侠事牵累,险遭大难。
宋神宗上台后,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所谓新法,本质是国进民退,把所有资源都垄断到政府,民间资本遭到扼杀,而且权力越集中国家财政收入越多,百姓就越贫困,官员腐败也就越厉害。新法行而天下民困,但王安石性情固僻,听不进不同意见,身边更聚集了一大批奉迎拍马、借新法发财的小人。熙宁年间,新法之弊愈深,有小吏郑侠把百姓苦况绘成了图,呈交神宗,神宗看了以后也大受感动,下诏废新法,结果吕惠卿、邓绾一班从新法中大捞好处的小人,跟神宗说:我们好不容易推行了新法,眼看国家要强大了,现在又要贸然取消,这哪行啊!于是神宗又改主意复行新法,并把郑侠下狱治罪,与郑侠交好的人都受到牵连。小山是郑侠的老友,当然也被抓了起来。他能安然出狱,是因抄郑侠家时发现小山所赠诗:“ 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张主繁华得几时。”神宗读此诗大为称赏,特诏释放。
郑侠曾受王安石赏识,但因不赞成新法,未获擢用。他以监门之小吏,绘图记新法祸民之状,上书神宗,被冠以反对新法的罪名入狱,用今天的话说,是“ 性质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小山的诗,如果深文罗织,可以说成是“ 恶毒攻击伟光正的新法” 的“ 现行反革命” ——“ 小白长红又满枝”,指新法小人在朝廷得势,“筑球场外独支颐”,指反对新法的君子投闲置散,“春风自是人间客,张主繁华得几时”,谓王安石的势位也不得长久,又能维持新法多久呢?用句“ 文革”流行语来说:“其用心何其毒也!” 幸好神宗没有做这样的“ 文本阐释”,若是遇到最擅长兴文字狱的明太祖、清世宗,小山不但不能出狱,一定还会被满门抄斩。
小山的朋友,除了郑侠这样的骨鲠之士,还有同样反对新法、列名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从一个人的交游最能看出这个人的本质,小山平素所善,都是风骨嶙峋的君子,则其品格为何如,自可想见。
小山致仕后,住到当年皇帝赐给他父亲的宅第中去,闭门谢客,不与权贵交往。当时权倾朝野、气焰不可一世的奸相蔡京,想要借重小山的声名,重阳、冬至二节,都派人造访,请小山填词,小山挥手而就《鹧鸪天》二首:
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风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初过雁,已闻砧。绮罗丛里胜登临。须教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觞滟滟金。
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间歌钟。云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开昨夜风。罗幕翠,锦筵红。钗头罗胜写宜冬。从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尊对月空。
二词应景应节,雅淡天然,却无一语颂扬蔡京,这是何等伟岸的人格!
天命之谓性,高贵傲岸,这就是小山的天命,是生来就具足的气质。黄庭坚说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诸公虽称爱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小山天资绝高,他绝非不明白一个真理:只有卑贱自处,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如鱼得水,但他宁愿陆沉下位,也不愿稍改自己的狷介,与这个荒诞的世界做哪怕一点点妥协。他的“ 疏于顾忌”,不是因为他不懂得,而是因为他永远不肯降志取容。这既是他的立场,也是他的天命之性。
人们很难想象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但其实诗人的勇决与思想家的沉潜本来并不矛盾。小山于儒学及诸子百家之学,皆能潜心玩味,他的论断非常高明,却决不以之博取声名。黄庭坚问他何以不多写些论学的文章,小山答道:“我平时处处注意言论,还被当代的这些名流忌恨,要是我把我所思考的东西都愤愤然地照直说出来,那不是直接把唾沫唾人脸上了吗?” 高贵的灵魂只要存在于世,就构成了对平庸者的威胁,尽管小山已经努力掩藏自己思想的优秀,还是不能不被平庸的名流巨公们所仇恨。他只有把一腔幽愤,都化为那些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的词作。
黄庭坚归纳小山平生有四痴:做官始终不顺利,而不肯向贵人大佬逢迎拍马,这是第一痴;文章保持自己的风格,绝不写一句歌功颂德的话,这又是一痴;万贯家财挥霍干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还像前辈隐士徐孺子那样,满不在乎,这又是一痴;别人怎样对不起他,他也不会记恨,信任一个人,永远不会怀疑对方会欺骗自己,这又是一痴。比诸晏殊的肤浅闲适,小山的身上才有着真正的富贵气象,他用生命实践着一位真正的贵族的人生。
古语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小山的身上,自然流露出的是极高贵、极纯净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天然地会让卑贱的灵魂恐惧颤抖。一种人,性情卑贱,是天生卑贱的功利主义者,他们活在世上为的就是蝇营狗苟,从最低的两餐一宿直到高官厚禄、娇妻美妾,永远都被生物本能所驱使,小山的至情至性,对精神世界的热爱,对高雅与美的沉浸,映衬出他们的生活的卑微可笑,因此仇恨小山;另一种人,见到高贵的灵魂会心生妒忌,他们不忿于别人可以这样毫无顾忌地生活,毫无顾忌地爱恨,毫无顾忌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此仇恨小山。尽管仇恨的程量无法估算,但后一种人,无疑是懂得小山的生命价值远高于一般人的,他们一面嫉恨小山,一面在内心深处也有着一份对高贵与高雅的企慕。后一种人对小山的恨,往往表现得更加刻毒。小山任颍昌府许田镇镇监时,缮写了自己的词,呈给府帅韩维(字少师) ,韩维本是晏殊的老部下,接小山词覆信说:“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其内心的嫉恨刻毒,在“ 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 十字中尽显无遗。
小山狷介高贵的品性,就像麝脐之香,无从掩藏。譬如其《玉楼春》:
清歌学得秦娥似。金屋瑶台知姓字。可怜春恨一 生心,长带粉痕双袖泪。从来懒话低眉事。今日新声谁会意。坐中应有赏音人,试问回肠曾断未。
这首词的立意,我认为是学习晏殊的《山亭柳·赠歌者》: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但即使题材相同、立意相似,小山词中都有一个明显的“我”在,他写词总会把自己的身世、自己的情怀寄托到歌者的身上,而晏殊对歌者的叙写却是冷静的、旁观的。这就是《小山词》远远高于《珠玉词》的原因所在。
无疑,小山是有精神洁癖的。除了那些同样不醉心功名、视利禄为浮云的朋友,他就只把青眼投向那些风尘中的歌女。他的好友沈廉叔、陈君龙家有莲、鸿、蘋 、云四位歌女,四位佳人的身上,没有达官贵人的装腔作势、鄙陋庸俗,她们一个个性若冰雪,才擅咏絮,与小山结成知己、腻友。小山每一词成,都交这四位佳人演唱,而小山则与沈、陈二君持酒听之,以为笑乐。多年以后,小山仍寤寐思之,怀而不忘。他的名作《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xīng )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 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讲的就是初见小蘋 ,所受到的艺术冲击和情感涟漪。小山不是见一个爱一个的花心大佬,他对莲、鸿、蘋 、云的感情是纯然艺术性的。他欣赏着也爱着她们,然而这种爱不是以占有肉体为目的,却是与她们一道,潜逃到一个灵魂的孤岛上,沉浸在艺术和诗歌所构建的房子中,忘记世间的牢愁失意。小山不是爱着某一位具体的女性,他爱的是爱本身。他的爱纯粹而高尚,因此也长久地感动着我们。
词的开始,小山营造出一种迷离惝恍的境界。“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是说春梦醒来,了无痕迹,宿醉初酲,恍如失忆。上着锁的高楼,低垂的帘幕,反映出的其实是主人公心窗紧扃,这个世界对他而言是百无聊赖的,他见不得绚烂的花儿凋谢,更见不得吹折花枝的狂风暴雨,“去年春恨却来时”,是说年年伤春,此恨无有穷已。
他忙于哀悼春光的短暂,美丽的不长久,他沉浸在这样一种哀伤的情绪中,落花微雨,沾身不觉,双燕低飞,心灰如死。幸好,还有艺术慰藉着他,带给他生意与温暖。“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本是五代时诗人翁宏的一首五律中的两句,原句在诗中毫不出彩,然而一用在词里面,就显得特别清壮顿挫,乃成千古名句。
过片“ 记得小蘋 初见,两重心字罗衣”,如电影特写镜头,定格住初见小蘋 时的讶异,也定格住小蘋 的永恒之美。所谓“两重心字罗衣”,是指衣领开襟,像是篆体的心字。其装束在当时必系时尚先锋,故小山才一见不忘。“ 琵琶弦上说相思”,非谓小蘋 对他一见倾心,而是说小蘋 弹奏琵琶、曼声低唱的,是相思的词作,这是当时词曲的普遍主题。小山对小蘋 ,是尊重与欣赏的成分居多,他能与这些歌女结下深挚的情谊,是因为他不论出身,只看灵魂,他欣赏小蘋 身上的艺术气质,更尊重小蘋 的灵魂。他比喻小蘋 行走时的仪态,仿佛彩云一朵,优雅轻灵。当初唱了什么、说了什么,可能都已忘却,唯有明月朗照着这位佳人像彩云一样飘去的情景,久久地铭刻在小山的心上。
小山特别擅长截取片断的、细节的场景来叙写情感。以视觉艺术喻之,小山词就像是一位高明的摄影家,他总是能捕捉到最让我们感动的画面,他把刹那化作了永恒。比如这首《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pán )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 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这首词没有交代女主人公到底是谁,只知她是一位歌女。但她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山与她的爱,浓挚、炽热,相思入骨。
上片记二人初相缱绻,快乐得不知复有人间。“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句法上语序错综,正常的语序则应是“ 当年彩袖殷勤捧玉钟拚却醉颜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曹孟德的英雄气概,红巾翠袖,行歌侑酒,才是文士的风流。眼前的佳人,绮年玉貌,彩袖底露出纤纤素手,捧着和手一样莹白的玉杯,递到跟前劝饮,谁还忍心拒绝她的殷勤?于是他甘愿一醉,醉了不要紧,因为他看见她盯着自己的眸子明亮如星。
小山是现实残酷竞争的失败者,但他的纯净与真挚,使得他可以收获那些位高权重的老爷们永远无法得到的真爱。女主人公显然对他一见倾心,因之为他倾情歌舞。“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二句,极言歌舞的凌风超月,因为她不是用歌喉来吟唱,而是用灵魂;她不是用身体在舞蹈,而是用生命。
相比上片的空灵婉约,下片陡转密实沉着。爱欲既炽,自然如胶似漆,即令不得不分别,别后也必相思无极,无有已时。爱情的美好之处,就在于双方既没有谁更快一步,也没有谁更慢一步,完美的爱,一定是同时堕入爱河,不需要一方苦苦追逐,一方再勉强接纳,千里万里,魂牵梦萦,不以时久地隔,始终默契于心。这才是爱的胜境。小山显然是享有了这样的爱情。“几回魂梦与君同” 一语,既见小山之深情,又见彼此相爱之殷,故此难得。“今宵剩把银 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化自杜甫的名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诗记战乱后的重逢,重大沉郁,欲说还休,小山词则轻灵飞动,一派天真,但深情眷眷,却与老杜一般心肠。
鹧鸪天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这首词译作白话,大概是:
歌女在酒筵上歌唱着动听的小令,就中一位最出色,芳名叫玉箫。她唱着《剔银灯》曲子,怎么那么妖娆!这样的佳人来劝酒,何妨醉倒!酒阑人散,归家的路上,酒劲儿未去,歌声还在耳畔萦绕。啊!这夜色多么宁谧美好。碧云天末,我还想念着她的容貌,可她却像巫山的神女,虚无、缥缈。罢了罢了!我这做着春梦的人儿,礼法且自全抛,快快踏着杨花,到谢娘桥边把妙人儿寻找。
这首词里有三个典故:“碧云天”用的是南朝江淹的诗句“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楚宫”则用宋玉《高唐赋》之典,略谓楚顷襄王夜宿高唐,有女子伴宿,自称系巫山神女,朝为行云,暮为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碧云天共楚宫遥”,整句是说我在思念着的佳人,却遥在高唐宫阙,无法相见。第三个典故是谢桥,即谢娘桥的省称。谢娘本指晋代的才女谢道韫,后指所眷女子。
这首词的结句写得清俊非常,但文字背后的精神气质更重要。这是破碎虚空,真正求得心灵自由的灵魂的咏唱。世人拘于礼俗,囿于成说,窘于衣食,远离自由久矣!因此,当世间终于出现一位自由的天才时,人们不是企慕、向往,而是震惊、诧异。理学家程颐听人诵此二句,不由失笑道:“鬼语也!” 虽说有赏识的意味在,更多的却是不信——不信世间有此自由之境,不信世间有此自由之人。
阮郎归
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绿杯红袖趁重阳。人情似故乡。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我认为这首词作于小山晚年,是他对自己哀乐过人的一生的总结。“天边金掌” 指朝廷宫阙。汉武帝好神仙,在宫门外立十二根大铜柱,号曰金茎,上有金人手捧露盘,是为仙人捧露盘,方士哄骗武帝,用露盘所承之露和着金泥玉屑服下去,可致长生。金色与下文的翡翠杯之绿、侑酒人衫袖之红,本来都是明亮的色泽,但一加以“ 露成霜” 三字,整个感觉完全变了。词人的情感基调是沉郁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故乡人情最厚,“人情似故乡” 一句,点出漂泊异乡内心凄苦之状,洒落中饱含热泪。过片“ 兰佩紫,菊簪黄” 二句句法非常矫健,它并不是“ 佩紫兰,簪黄菊” 的倒装,而“ 兰宜佩紫,菊应簪黄” 的省略。唐宋时不管男女老幼,在重阳节时都会在头上插满黄花,身上有时候也会佩着兰草,这是许多人一年中难得放浪的一天,小山又怎样呢?他“ 殷勤理旧狂”,过往的生命,像电光石火一样,在他的心头飞快掠过,他追想自己狷介的一生,不肯俯仰贵人门前,坚守自己的原则,有所不为,终落得沉沦下僚,无以仕进,此时此刻,他后悔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非但不后悔,甚至更有一种隐隐的骄傲,一种悲凉的、承受悲剧命运、担荷世界罪恶的骄傲,这才有“ 理旧狂” 的“ 殷勤”。
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他的生命是悲凉的,然而又是丰盈的、充实的,这种悲凉贯穿了他的一生,并感染着九百年以后的我们。
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小山这两句词不是写给他自己,而是用来抚慰他所有的读者,抚慰所有被他感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