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04-02Ctrl+D 收藏本站
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能弄清楚过。其中之一便是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文人的工作量。
现在,从事写作一行的人们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可以写出三四千字。可是,莎士比亚有10多种工作分散他的精力,还有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婆,鹅毛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出37个剧本呢?
再有,“无敌舰队”的老兵洛浦·德·维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从哪儿弄来所需的墨水和纸张,写下1800部喜剧和500篇文章的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小房子里有20个孩子吵吵闹闹,而他居然有时间谱写出5出清唱剧、190首教堂大合唱、3首婚礼大合唱、12支圣歌、6支庄严的弥撒曲、3支小提琴协奏曲(仅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史册了)、7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3支双钢琴协奏曲、2支三钢琴协奏曲、30首管弦乐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低音提琴、法国圆号写了曲谱,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这样的画家要怎样勤奋用功,才能在30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创作4幅油画或4幅蚀刻画呢?像地位不高的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是如何在一生中制作出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的呢?
我现在不是在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那么多的情节,听出那么多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样的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出那么多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他们的体力。他们是如何胜任的呢?难道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也不抽出几小时打打台球吗?他们从不疲倦吗?他们听说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17世纪和18世纪到处都是这种人。他们无视健康法则,照样吃喝那些有害身体健康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作为光荣人类的一员所肩负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的艺术与才智成果实在是令人惊叹。
艺术和科学的情形也出现在繁琐且需要仔细推敲的神学上。
如果你在200年前,走进任何一座图书馆,就会发现从地下室到顶楼上摆满了8开本、12开本和18开本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和纸张装帧,上面附有尘土,早已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些书都包含着广博的或许又无用的学识。
在现代人看来,这些书籍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诸多字词已经失却了意义。可是这些发了霉的汇编却有着重要的目的。就算是它们一无是处,至少还是清洁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使相关人士普遍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并不是逻辑推理和辩论所能确定的,倒不如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这听来仿佛是讽刺挖苦式的夸赞。不过我希望将来30世纪的批评家们在研读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能够同样仁慈。
巴鲁克·德·斯宾诺莎是这一章的主角,他在数量上没有追随当时大写特写的风气。他的全集不过是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
但是,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所必需的大量学习,会拖住普通的健康人的后腿。这个可怜的结核病患者的早逝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因为他试图用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却没有受过住进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的一个行省。西班牙征服此地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迫使国家陷入衰败之境。斯宾诺莎一家也被迫离开了旧家园,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套房子,辛勤工作,积存了些钱财,没过多久,就成为“葡萄牙移民区”中最受尊敬的人家之一。
如果说这家的儿子斯宾诺莎意识到了他们的犹太血统,那么除去邻居小孩的嘲笑,更要归结于在塔尔穆德学校受到的训练。由于荷兰共和国充满了阶层偏见,无暇顾及种族偏见,因此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容身之地,过上平静而和谐的生活。这是荷兰生活的特色之一。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不会忘掉这一点,这是有充足原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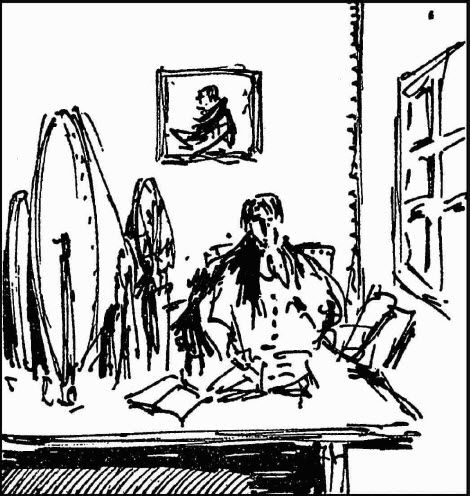
斯宾诺莎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当晚的时候,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是极不令人满意的。双方之间的争吵简直到了不可解决的程度,因为双方都各有正误,而且都声称自己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这本书里已经说过,专横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按照这个理论,显而易见,只要忠诚于各自的宗教,基督徒和犹太人就会认为对方是敌人。首先双方都坚持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他民族的其他上帝全是冒牌的。其次,双方是危险的商业对手。犹太人来到西欧,就像他们最初抵达巴勒斯坦一样,是寻觅新家园的移民。当时的工会即“行会”,不让他们找到职业,所以他们只好开个当铺和银行作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这两种行当在中世纪很相近,在人们眼里,体面的市民是不会投身到这些行业的。直到加尔文时期,教会一直对金钱(税收除外)深恶痛绝,而且把拿利息看成是一种罪孽,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当然,高利贷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容忍的。早在4000年以前,巴比伦人就曾通过一条严厉的法律,对付那些想从别人的钱中牟暴利的金钱交易者。我们从2000年前写下的《旧约》的好几章中,都可以读到,摩西曾经明确禁止追随者以高利息借给别人钱,不过借给外国人不在此列。后来,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内的伟大的希腊哲学家都表示,不赞同从别人的钱中生出钱来。教会神父对这种事情的态度越发地明确。在整个中世纪中,放债人一直被人看不起。但丁甚至在他笔下的地狱里为他的金融界朋友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壁龛。
从理论上或许可以证明,开当铺和开银行的是不受欢迎的市民,世界要是没有他们,该有多好啊。不过,只要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农业国,那么不用借贷,哪怕是最简单的生意都做不下去。因此,放债人成了社会需要的魔鬼,而注定要下地狱的犹太人(按照基督徒的看法)被迫从事人们需要的职业,但体面人绝不会染指。
这样,不幸的流亡者被迫进入了不光彩的行业,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对头。他们刚一发迹,对方便翻脸无情,转而反对并谩骂他们,把他们锁在城市中最肮脏的区域,冲动之下还会把他们作为不信教的恶棍绞死,或是作为叛逆的基督徒烧死。
上述行径真是愚蠢,而且无知。无止境的攻击和迫害并没能使犹太人喜欢基督徒。直接的后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退出了公共交往领域,成千上万天资聪颖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艺术和科学中一展身手,却把脑力和精力浪费在了无用的研究那些深奥莫测的难题和引发诡辩的旧书上,数百万无依无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臭气烘烘的小屋里过着畸形的生活,一方面听长辈们讲他们是肯定会继承这个世界及其财富的上帝的子民,一方面却又不停地听到别人骂他们是猪,只配上绞架或刑车,并因此恐惧得魂不附体。
要让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们(不管是谁)保持用正常的视角看待生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当他们愤怒到极点时还起来反抗压迫者,结果他们又被称为“叛徒”“忘恩负义的恶棍”,遭受更严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有一个结果:增加了心怀怨恨的犹太人,也让其余的犹太人意志颓丧。一言以蔽之,它使犹太区成为受挫的雄心和累积的仇恨的可怕的聚居地。
斯宾诺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遇到大部分族人生来就承受的苦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去读书,学会了希伯来文的动词变化之后,立刻被送到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儿,研读拉丁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
弗朗西斯科博士,恰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相传他是卢万大学的毕业生。依照城中学识最为广博的教堂执事的说法,他其实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不过这是一派胡言。弗朗西斯科博士年轻时确实在一所天主教的学校度过了几年时光,但他并不醉心于此。后来,他离开家乡安特卫普,抵达阿姆斯特丹,并在此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拥有卓绝的因材施教的能力,善于想办法使学生们喜欢古文课程。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民不在乎他曾经与天主教的瓜葛,都甘心情愿且颇为自豪地把孩子托付给他。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在六韵步诗和静词变格上总是强于其他学校的学生。
范·登·恩德教授小斯宾诺莎拉丁文。另一方面,由于他还热心地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毫无疑问,他会教给小斯宾诺莎不少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会提到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一起寄宿学校,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使家人非常惊喜,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教授,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有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选购了哲学书。
其中,有一个作者令他尤为感兴趣。
这个人便是笛卡尔。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征服欧洲的穆罕默德。笛卡尔不满10岁就被送到耶稣会接受教育了,并在那里度过了12年。笛卡尔很招人讨厌。因为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拒绝接受那些未经证明的东西。耶稣会会士也许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对付这种难调教的孩子的人。他们不但不挫伤孩子,还能将其培养得很成功。要检验布丁就要品尝品尝。检验教育的成果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个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20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从头到尾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青年的进修学院。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像犯了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感兴趣的是数学和炮术,而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刚一结束,他便辞了职,前往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了一段时间的仗。
但是那次战役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唯一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返回法国,想学一些高级的攻坚战术。可是他厌倦了军营生活。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打算结婚,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想过宁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居所。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现存的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并不困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20个小时)用来工作。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似乎过于枯燥。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对这种自我折磨的放逐生活很是满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其实距离真正的科学还很远很远,不首先铲平陈旧的错误和荒谬,普遍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事一桩。不过笛卡尔很有耐性,到了30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不偏不倚,这使得天主教徒骂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骂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也丝毫没有干扰他的工作。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在那里与世长辞。
在17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做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公元1680年是一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这等于宣称自己是既定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信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相提并论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痴狂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祖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是没有人提的。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问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这种观念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存在,结论就是必然的——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案件,并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毅然放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父辈的宗教信仰。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在腰边佩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接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傲慢使他惊讶和愤怒,而且他也很自高自大,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样狭小的社会组织里,这种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孤傲的梦幻者,这些人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则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者。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亵渎神圣的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产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得到澄清,控告随后撤销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叛者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道。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犹太群体。但是他要首先公开认罪,任教区全部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种羞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这次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被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玷污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悄悄地遮掩此事。他们找斯宾诺莎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继续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固定的年金。
斯宾诺莎可是个不肯妥协的人,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不给人一点儿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房间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终结掉他的生命时,他也拒绝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显然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短短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气急败坏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求和市长会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颇受人尊崇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人们有个好习惯,对整个事情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处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令的事,便如实向市政府的官员们作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青年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静无波,就像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打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随着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曾有传言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恋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孩子才10岁,所以这个传言似乎不是事实。
他有几个好朋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些资助,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研究。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情愿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80块钱的接济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过着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清贫生活。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委婉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最终回绝了,继续过着平静而愉悦的流亡日子。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迁到海牙。他的身体一向欠佳,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微末损伤了他的肺脏。
公元1677年,他孤独而急促地离开了人世。
使当地教士非常愤怒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他的墓地。两个世纪之后,当纪念他的雕像揭幕的时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去保护参加这个庄严仪式的人,使他们不被成群的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伤害。
这就是斯宾诺莎,他有什么影响呢?他难道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一堆一堆的书里,说出的言辞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色发青的勤奋的哲学家吗?
不,他不是。
他取得的成绩,绝不是依靠发挥才智或凭借巧言善辩得以正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斯宾诺莎之所以伟大,主要靠他的勇气。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只知道一条法则,它是在早已被遗忘的遥远的黑暗年代里定下的不可更改的死规矩,这些规矩是为那些自认为能够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阶层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
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知识自由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无政府几乎是同义词。
他知道他的逻辑体系既会得罪犹太人,也会得罪非犹太人。
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把所有问题都看成普遍问题,无一例外地视其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相信这些问题是纯现实的表现,它将适用于最后审判日,就像适用于创世纪那样。
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斯宾诺莎像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窄界线,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勇敢地构建起自己崭新的思想体系。
如此一来,他恢复了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以来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正的世界一员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