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新天国
04-02Ctrl+D 收藏本站
没有什么理由害怕斯宾诺莎的作品会广为流传。他的书很像三角学教科书那么有趣,然而很少有人能读三个句子以上,不管是哪一章节。
需要另一种人向广大群众传播这种新思想。
在法国,国家一旦转为君主专制,独立思考和调查的热情便会戛然终止。
在德国,30年战争带来的是穷困和恐怖,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至少有两个世纪之久。
17世纪后半期,英国是欧洲大国中在独立思考领域有进步可能的唯一的国度,国王与国会的长期争论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这就促进了争取个性自由的事业。
首先我们要谈谈英国国王。多年来,这些不幸的国王始终夹在魔鬼般的天主教和深海般的清教徒之间。
天主教的臣民(包括许多暗地里投靠罗马的圣公会教徒)一直叫嚣要返回到英国国王当教皇的仆从的幸福时代。
而清教徒臣民却用另一只眼紧盯着日内瓦,梦想英国有一天没有国王,英格兰变得像潜藏在瑞士山脉角落里的幸福联邦一样。
但这不是所有。
统治英格兰的人也是苏格兰的国王,苏格兰臣民在宗教事务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要求。他们完全相信自己坚决反对宗教信仰自由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新教徒的领地范围内有其他教派存在,还能自由信仰,这简直是邪恶。他们坚持认为,不仅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教徒应该被逐出不列颠群岛。而且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总之所有对活生生的上帝的存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应该一律绞死。
但是,这个三角冲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些人想在对立的教派之间保持中立,便不得不缄口少言,这使他们变得比原来宽容些了。
如果斯图亚特和克伦威尔在一生的不同时间里都坚持各教派的平等权力——而且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也这样做了——那绝不是由于他们对长老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徒有什么感情,或者是他们受到那些教徒的拥戴。他们只是在一个十分困难的交易中争取最好结果。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里的一个教派最终变得非常强大,这件可怕的事情告诉我们:如果英国的众多相互竞争的小教派中的一个教派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绝对专制,那么英格兰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
克伦威尔当然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但是这个护国公非常睿智。他知道他的统治是靠铁军维持的,便小心地避免一切会使反对派联手对付他的极端行为或法令。不过他的宽容之心也就到此为止。
至于可怕的“无神论者”——也就是前面所述的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和其他人类神圣权利的信徒——他们的生命仍然像以前那样难保。
当然啦,英国的“自由思想派”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毗邻大海,只需要能忍受36个小时的晕船就能抵达安全的避风港——荷兰诸城市。荷兰城市里的印刷所出版南欧和西欧的违禁文学,穿越北海就意味去出版商那儿赚得一笔稿酬,再看一看思想反抗文学中有什么新鲜东西。
有些人利用这个好机会进行安定的研究和宁静的思索,其中最有名望的当属约翰·洛克。
他和斯宾诺莎同一年出生。他像斯宾诺莎(其实也像大部分独立的思想家)一样,是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的儿子。巴鲁克的父母是正统的犹太人,约翰的父母则是正统的基督徒。他们用不同教旨的严格教义培养孩子,当然他们是好意。不过这样的教育要么摧毁孩子的心灵,要么就是使其变成叛逆。约翰和巴鲁克一样,都不是顺从的人,他紧咬牙关离开了家园,独自去谋生路。
洛克20岁那年,来到牛津大学,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笛卡尔的思想。可是在圣凯瑟琳大街尘土堆积的书店里,他发现了其他一些更合乎口味的书籍,比如说,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
霍布斯是个有意思的人,他在马格达朗学院做过学生,总也不肯安分守己,去意大利和伽利略谈过话,与大名鼎鼎的笛卡尔通过信。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欧洲大陆,为的是躲避怒火冲天的清教徒。偶尔他写一部长篇巨著,把他对所有可以想到的题目的看法都包罗进去,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书名:《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老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
这部博学的著作问世的时候,洛克正在大学里上二年级。该书一针见血地指明了王侯的本质、权利,尤其是他们的责任,就连最彻底的克伦威尔派也不得不赞同,许多克伦威尔党徒都觉得应该宽赦这个一向抱怀疑态度的人,因为他尽管是个保皇派,却在一本重量不在2267克左右以下的书里揭露了保皇派的矫揉造作。当然,霍布斯不是那种易于归类的人。当时的人称他是“不拘于教条与形式的人”,意思是说,他更感兴趣的是基督教的伦理学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与纪律,主张给予人们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洛克与霍布斯有相同的气质。他至死都留在教会里,但又从内心里赞成对生活和信仰应作宽容的解释。洛克和朋友们认为,国家摆脱一个暴君(头戴金冠的),如果只是为另一个暴君(头戴黑色宽软帽的)来滥施权力,那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今天否认这一派教士的忠诚,而第二天又接受另一派同样傲慢专横的教士的统治呢?从逻辑上讲,洛克等人的观念当然是对的,不过有那么一伙人,对他们而言,如果“自由人”一旦成功,把僵化的社会体系变成伦理辩论的社会,他们就会丢掉饭碗,因而这个观点在他们当中是行不通的。
洛克本人似乎具有极大的人格魅力,他有一批颇有势力的朋友,能保护他不受执法长官的怀疑,但是没过多久,他还是不能再逃避“无神论者”的嫌疑了。
这发生在公元1683年的秋天。洛克只好前往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已去世五六年了,不过荷兰首都的学术气氛一直十分自由,洛克有机会学习和写作,而且不受官方的干扰。他很勤奋,在外的4年里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信》,这使他成为我们这本小历史书的主角之一。在信中(按照他的对手的意见应该是三封信),他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国家干涉宗教的权利。洛克认为(他在这方面的观念,源于另一个流亡者,法国人皮埃尔·贝尔,那时他住在鹿特丹,正在一个人编撰百科全书,很有才学),国家只是个保护性的组织,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为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号施令、让人信仰这个而不允许信仰那个,洛克和他的信徒始终没有搞明白。国家并没有规定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非要强迫他们去这个教堂而远离那个教堂不可呢!
清教徒主义的不彻底的胜利使16世纪成为奇特的宗教妥协的时代。
威斯特法利亚的和平终止了所有的宗教战争。它阐明了一条道理:“所有臣民都应该服从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一个六等公国的臣民今天全是路德教徒(因为当地的大公爵是路德教徒),而在一个七等公国中,他们摇身一变又都成了天主教徒(因为当地的男爵恰好是个信奉天主教的人)。
洛克分析说:“如果国家有权指定人们的灵魂归宿,那么一半人都注定要沉沦,因为不可能两种教派都正确(按照宗教手册第一条的说法),生在边界这边的肯定会进天堂,生在那边的注定要坠入地狱。这样一来,出生时的地理位置便能决定一个人的灵魂能否得到拯救了。”
洛克没有把天主教徒列入他的宽容计划中,这的确是件憾事,不过可以理解。在17世纪的不列颠百姓眼里,天主教并非一个宗教形式,而是一个政党,从来没有停止颠覆英国安全的阴谋,它建造了个“无敌舰队”,还弄来大桶大桶的炸药要把这个所谓友好国家的国会摧毁。
因此,洛克宁愿主张把权力交给殖民地的异教徒,也不给天主教徒,而且要求他们别再踏上英国的国土。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危险的政治活动,并非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同。
要听到这种看法就必须倒回16个世纪。一个罗马皇帝曾经定下著名的原则:“宗教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上帝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英国人在不到60年里经历了四个政府的更迭,所以他们较容易接受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公元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渡过了北海,洛克也紧跟着他坐船来了,同船的还有英格兰王后。从此,他的生活平静无事,高寿到72岁才与世长辞,成为备受人们尊敬的作家,不再是骇人的异端了。
内战是件可怕的事,却有一大好处。它可以净化气氛。
17世纪英国的政治纷争耗尽了这个国家的多余精力。当其他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偶尔有一个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击现存的教会,像丹尼尔·笛福,这也许会倒霉地触犯法律。不过《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被戴枷,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历来天生就是对讽刺疑心重重。假如笛福写的是严肃地维护宽容的文章,也不会身受惩戒了。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化为一本半幽默的小册子,名叫《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这表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低俗之辈,低俗到跟监狱中的小偷差不多的地步。
笛福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旅行从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他被专横地赶出发源地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很受欢迎的安身之所。与其说这应该归因于刚刚搬进那方土地的人们的性格,倒不如说是因为新大陆比旧大陆具有大得多的经济优势。
英格兰是个人口稠密的小岛,只能为大部分人提供立足之地,人们如果不愿意再践行古老而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则,所有的生意都会终止。但是在美国,它是一个范围不知有多大、财富多得不可思议的国家,是一个只住有为数不多的农夫和工人的大陆,这种妥协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因此,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团体里,居然产生了防范坚固的自诩正确的正统教派,自从加尔文在瑞士西部充当了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的快活日子以来,这种情况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查尔斯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长期地居住上了人,这一小伙人被称为“朝圣神父”。朝圣者一般是指“为表达宗教虔诚而去圣地旅行的人”。按照这个意思讲,“五月花”号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们是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他们憎恨那些墨守成规的、崇拜天主教教义的信徒,因此离开了英国。

新的天国
他们首先渡过北海来到荷兰,到达这里时恰好赶上经济大萧条。我们的教科书还继续讲述说,他们要继续航行是因为不愿意让孩子们学习荷兰语,否则就会被这个国家同化。这些朴实的人居然不图报恩,却跑去做什么美国公民。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住在贫民窟里,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国家里难以谋求生路。据说在美国种烟草的收益远胜于在莱顿梳羊毛,于是他们便前往弗吉尼亚。没想到遇上了逆风,马萨诸塞岸边的水手驾驭船只的能力又有限,他们便决定就地住下,不再乘着漏船到海上的恐怖中去冒险了。
这些人虽然逃脱了淹死和晕船的难关,却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大多是英国内地的小城镇的人,没有闯荡的能力。他们的共产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热情被不息的狂风吹得冰冷,妻子和孩子由于没有像样的食物而饿死。只有很少的人熬过了三个冬天存活下来,他们秉性善良,习惯于家乡那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可是由于随后又来了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湮没了。那些后来的人无一例外全是更严厉、更不妥协的清教徒,他们把马萨诸塞变成查尔斯河畔的日内瓦,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清教徒们在弹丸之地上挣扎谋生,总是处于灾难的边缘,他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从《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据。他们与体面的社会和图书隔绝,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摩西和纪登传统的继承人,很快会成为西部印第安人的马卡比。他们没有办法慰藉自己这艰苦乏味的生活,只能相信他们受苦受难是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还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他的人都错了。谁要是含蓄地指出清教徒的做法和想法并不完全正确的话,便会由于观点相异而遭遇虐待,不是被无情地鞭打一顿赶到荒野里,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驱逐出境,除非他们万幸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藏起来。

新大陆的寒冬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没有丝毫贡献,它起的作用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歪打正着,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中也是常见的。宗教专制的暴力引起了更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力。在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教士暴政以后,涌现出新的一代,他们是形形色色的教士统治的公敌,认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他们对于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体的做法很是厌恶。
这个发展过程非常缓慢,却颇有运气,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爆发之前危机才出现。结果是,起草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注入了一些很是现代的原则。经过事实验证,这些原则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具有巨大的价值。
可是在这之前,新大陆在宽容领域里已经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居然是在天主教区里!在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这次有意思的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卡尔佛特父子,他们的祖籍是佛兰芒,不过父亲后来移居到了英国,为斯图亚特王朝效劳,作出了显赫的贡献。他们最初是新教徒,但是乔治·卡尔佛特——他做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和总管——对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烦透了,便又回到旧有的信仰。旧有的信仰好也罢、坏也罢、还是不好不坏,反正它称黑为黑,称白为白,不把每项教义的最后判定权留给一群半文盲的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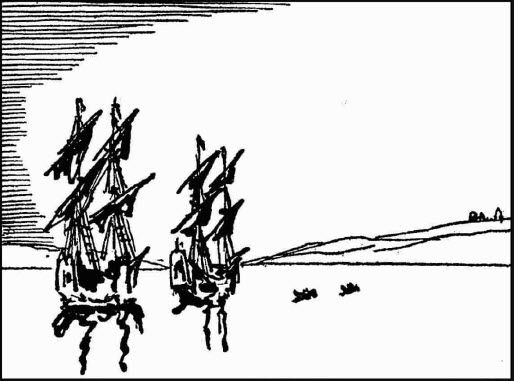
马里兰的奠基
这个乔治·卡尔佛特看起来多才多艺,他的倒退行为(那时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并没有使他丧失国王对他的恩宠。相反,他还被封为巴尔的摩的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为遭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得到了各方的帮忙。他先在纽芬兰试了下运气,但是他派去的定居者都无功而返。于是他申请在弗吉尼亚要几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谁知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也不肯同这些危险分子做邻居。巴尔的摩男爵接着要求得到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没等到获批就归西了。他的儿子塞西尔继续这件好事,公元1633年至1634年冬天,“方舟”号和“鸽子”号两条小船在乔治的兄弟伦纳德的指挥下,穿过大西洋,于1634年3月满载着旅客平安抵达切萨皮克海湾。这个新领地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叫做马里兰。亨利四世本来打算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这计划却被一个发疯的教士用匕首打破了——这个疯癫者用匕首刺杀了亨利四世。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妻子,而这个国王不久又在清教徒手里丧失了性命。
这块移民区非同一般,它不消灭印第安人,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平等相待。但本身却经历了好多艰难岁月。首先,移民区里住满了很多圣公会教徒,他们都是为了逃避马萨诸塞清教徒的蛮横与残忍才来的。后来清教徒也闯进这块移民区,为的是逃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残暴。这两伙人都是逃亡者,盛气凌人,都想把自己那套所谓的“正确信仰”强行加给这个刚刚给他们安身之处的地方。由于“所有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在马里兰的领地上都被明文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权力要求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安安静静别惹事。但是,不久之后,英国本土的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爆发了,马里兰人便担心无论哪一方获胜,他们原有的自由都会丧失。因此,公元1649年4月,刚刚获得查理一世被处决的消息以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倡议下,就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其中有这样一段规定,很精彩:
“由于宗教对思想的高压统治在所及的范围内常常产生有害的结果,为了本省份政权的安定,为了保护居民之间的友爱和团结,特此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为理由,对本省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进行干预、骚扰及迫害。”
在一个耶稣会会士掌管重权的领地里,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这显示了巴尔的摩家族杰出的政治能力和不可小觑的勇气。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称赞。后来,一撮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马里兰的政权,《宽容法》被废除,代之以自己的《关于宗教的法案》。该法案给予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充分的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并不包括其中。
幸运的是,这个反动的时期并不长。公元1660年,斯图亚特王室复辟,巴尔的摩派的人也重新掌握了马里兰的大权。
对他们政策的又一次攻击来自另一边。圣公会教徒在英国本土获得了完全胜利,因此坚持要让自己的教会变成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卡尔弗特家族继续战斗,但他们却看到不大可能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这一边。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才宣告终止。
新教徒获胜了。
专横也占了上风。